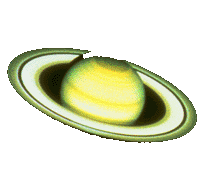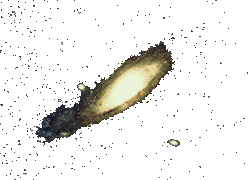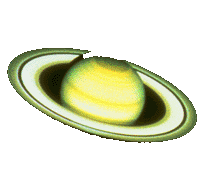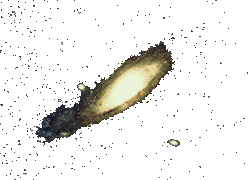|
近日听说:老店大芳斋的牌子又挂了出来,这勾起了我三十多年前的记忆。
那时的大芳斋在观前街东头的临顿路上,我家就在附近的一条巷子里。因为近,就时常光顾该店,也有了较深的印象。
当时的节奏不快,苏州人的生活又很悠闲,下午三点后就该吃点心了。每天下午放学后外婆常让我去大芳斋买肉包子。这可是件美差,不光能早点闻到肉的香味,还能先吃为快,那个香,现在想来还谗。
卖包子的是个胖阿姨,很小的一个窗洞,包子四分钱一个,我常买六个,好婆、我、表妹各两个。往往包子没到家,我的两个就光了。当然大芳斋最好吃的不是肉包子,而是汤包。起码我是这么认为的。
一般吃汤包是在星期天早晨,由大人们带着去。堂内很大,一式的八仙桌加长条凳,我们总是选堂中靠北的桌子坐。因为那里邻近出货口,取汤水方便。
我的食量比较大,照例是壹碗三两的白汤爆鱔面加壹客汤包,共四两。我对大芳斋的面印象一般,因为它与其它的面店相比有一股烟糠气。听懂行的人讲是由于灶头没砌好的缘故。反正在我光顾的几年中面一直有烟糠气,这几乎成了一种特色。汤包则不同了,简直可以用“享用”二字来形容。
大芳斋的汤包二角钱壹客,共八只。跑堂的师傅端面是吆喝着“两两碗来哉”,手臂托着一摞的面碗到食客跟前放下的,汤包则往往是双手端来的。一只手掌般大的白瓷盘上放着八只一般大的汤包。看上去嫩白整圆,很是可爱。吃汤包照例有一碗汤,这碗汤需自己端。我们的座位离给汤的桌子很近,又是我吃,自然是我去端。给汤的是位高个子师傅,见我去就会拿出一只白瓷饭碗,从汤锅中舀一勺倒入碗内,然后从手旁的一只白搪瓷盆中抓一撮蛋皮放入。现在想来其实是一碗白开水蛋皮汤,但这是享用汤包的一部分,是缺不得的。
因汤包是温在笼格中的,而面则要下起来,所以常常是汤包先到,一桌子数我最先吃。单只汤包除底部有时可见一个小的收口外其余部分圆糯光平。我是不敢一口咬破的,否则准被里面的汤汁烫伤了舌尖,那样就有一段时间麻了。汤包的皮就那薄薄的一层但居然没有汤水渗出,实在是奇事一桩。这样皮是皮、汤是汤、肉是肉,吃一只汤包就能获得三重滋味,实在是味道好极了。先说皮吧。那皮里外面口感是不同的:外面淡而里面浓,轻轻咬上去还有弹性。因汤包内的汤汁浸润而使里面和外面的口感对比十分显著。再说汤吧。吃大芳斋的汤包,讲究的是吃法:首先要咬开一个小口子,这样便于吸汤。那汤汁甜而不腻,咸淡适宜,鲜美无比,毫无油腻之感。我也一直搞不明白:店里的馅是怎么做的,一蒸就会出来这么多汤水,自己家怎么就做不出?后来一打听,据说要放什么冻水,这就搞不清楚了。最后说说那肉馅,可是肉香扑鼻啊。这肉香在没咬破汤包皮时是闻不到的,当一咬破就会顺着破口而透出,闻来醇厚无比,吃来肥嫩得当,满齿生香。这时如觉得口干,则可饮汤解渴,也只有到这时才能感到无味白汤的妙处:吃了鲜咸甜香的汤包,正需它来冲味。接下来上来的面就基本属于填饱肚子的了。
许多年过去了,我对许多美食的印象均已淡忘,惟独大芳斋汤包的滋味却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,因为以后我再也没吃到类似的美味。或许这只是我童年胃口好时的感觉?就不得而知了。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