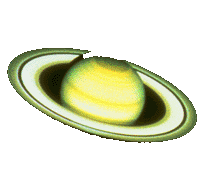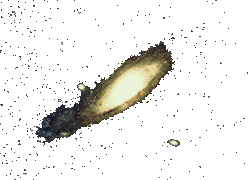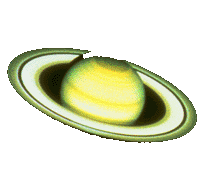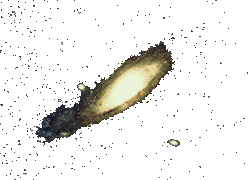|
版 本
■ 唐弢
谈起校勘,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版本。段玉裁说,校书之难,难在于定底本之是非,这就进一步说明了要和书籍打交道,多少需要懂得一点版本学。
所谓版本,原来只是指雕板印行的书,以之区别于写本或碑刻。自从印刷术发达之后,刻书例用木板,这板或那板之间,互有异同,于是版本的含义也随着扩大,索性把抄的、拓的、印的都包括在内,鉴别审定,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。这种学问的特点是要根据书籍的纸张、墨色、字体、版式等等,区分时代,辨明地域,从而研究何者是原刻,何者是翻刻,何者是旧抄,何者是新抄,借以判断其内容如何,是否善本……等等。有些熟悉版本的人,对于每一部书的传抄先后或雕板源流,都能说得清清楚楚,甚至连各种本子的行款——每页几行,每行几字,也莫不一一记住,可以背诵如流,不差分毫。
这些专家之娴熟版本,大抵是多看多记,全凭经验得来,对于书的内容,反而有点茫然,所以他们的所谓善本,有时却未必可靠。按照张之洞的说法,构成善本有三个条件,第一是足本,即完整不缺;第二是精本,即校印无讹;第三是旧本,即旧刻初印。丁松生也在《善本书室藏书志》里列举四条:曰旧刻,曰精本,曰旧抄,曰旧校;而他的所谓精本又只限于明代嘉靖以前的刻本,可以说完全着重在一个“旧”字。缪荃孙制订的善本定义更为荒谬,他的主张是:
一、刻于明末以前者为善本,清朝为民国刻本,皆非善本。
二、钞本不论新旧,皆为善本。
三、批校本或有题跋者,皆为善本。
四、日本及朝鲜重刻古书,不论新旧,皆为善本。
从前有人说过: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。这是因为明代自万历以后,刻书者众,往往炫奇猎异,互相竞争,或则更换书名,或则改动内容,将古人著作随意糟蹋,把读者弄得莫名其妙。属于前者,例如郎奎金刻《释名》,改名《逸雅》;冯梦祯刻《大唐新语》,改名《唐世说新语》;《北堂书钞》初改为《大唐类要》,再改为《古唐类范》;收入商濬《稗海》里的《蒙斋笔谈》,其实不过是《岩下放言》的节录,而著者叶梦得却被改作郑景望,岂非荒唐之至。属于后者,顾炎武在《日知录》里谈得最多,如把骆宾王《为徐敬业讨武纷檄》里的“伪临朝武氏者”,改为“伪周武氏”;把曹丕《短歌行》里的“思我圣考”,改为“思我圣老”,又妄评之曰:“圣老字奇。”最突出的是,山东人刻《金石录》,见李清照后序“绍兴二年玄”。
|